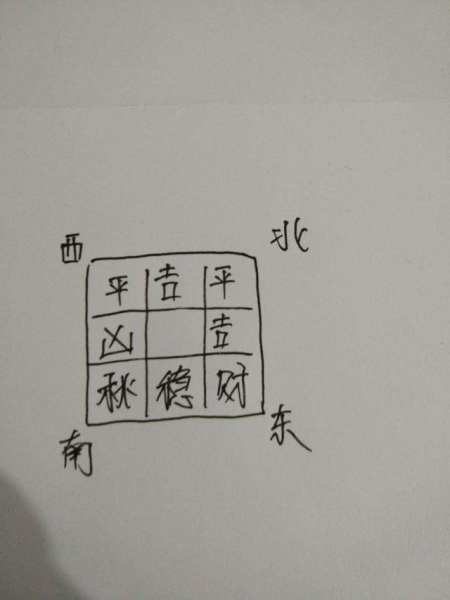困于系统、囿于平台的我们,如何自处?
从打车app爆出恶性事件,到外卖平台“挤压”骑手,再到某公寓平台爆雷,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被关注,学界也一直在关注平台企业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最近,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平台、技术与传播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试图讨论平台经济的现状和未来。
打破“平台”概念才能跳出不平等体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邱林川教授首先分享。他梳理了平台的发展历程,在21世纪之初,人们对新闻门户网站这类平台还抱有美好的想象,平台被神化为一个政治中立、经济平等的世界。
然而时过境迁,问题日益暴露,平台开始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在这里,劳动者被压榨,消费者被欺骗。但邱林川试图反思这种泛滥的批评。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平台都会追随资本的逻辑,也有一些公众参与组织的平台,例如维基百科等,靠的是公众的集体参与生产知识。
邱林川认为,平台这个词只有被打破,才能跳脱出不平等的社会体系。他认为,我们可以用Utilities、Public service media、Commons再建构对平台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引入是一种对公共性的引入,指出了平台并不一定皈依资本的可能。
邱林川希望跳出传统的研究框架,指出“世界地方主义”的发展视角。 不同于“全球地方化”强调自上而下,从全球渗透到地方的文化过程,“世界地方主义”强调资源的共享,实现共享的制度。世界地方主义可实现一种将小规模的韧性社区,同开源运动的社区形式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一种“设计全球化,制造地方化”的“另类”平台的种子形态。邱林川认为可以从地方政府着手,让地方政府看到这类平台的作业,积累经验,迎接资本主义平台内爆危机之后的可持续发展。
邱林川说,这种想法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GitHub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他继续说,当今推动政府治理的社会运动的局限性在于,人们日益陷入身份政治的对立之中,运动的诉求依然要指向政府,而很多政府都面临着被资本控制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认为,另类平台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补充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激进左翼则认为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带来资本主义的巨变,”邱林川说,“而改革派的立场比较温和,他们看到主流平台之外的危机与机遇,他们认为平台可以利用科技,对资本进行内外结合的改造,从而实现资本为公共利益和政府服务,而政府为社区服务的新形态。”
外卖平台从“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算法生产
社科院新闻所的孙萍以外卖行业为例,关注算法对于平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孙萍研究了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过程。例如,在平台配送时长算法的严密计算中,时间和空间发生了折叠,“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目标精准到每个配送员的身上。
孙萍不仅关注数据科学里的算法,也关注社会科学里的算法,即关注算法所形构的社会权力关系以及算法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孙萍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这个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gency),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网络”并不单纯指代互联网或社会网络理论,它指代一种本体论的认知,具体说来,是一系列行动的组合体,网络的参与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物流链、交通工具等在内的非人行动者。
孙萍发现,平台的“算法初转译阶段”主要是培养人们吃外卖的习惯。无论是消费者和商家,还是物流、交通、网络都会被卷入这个阶段。算法在这个阶段也经历了从人工派单模式到系统派单模式,再到云端分组派单模式最后到深度学习智能模式的转变。
算法的“加速生产阶段”引入了更多的速度与竞争。2017年以后,外卖半台迎来爆发式发展,竞争也日趋激烈。在此期间,平台间核心的竞争变成了对“按需服务”的强调,高效便捷成为了强制要求。比如有“XX外卖,送啥都快”的广告词,或者如果骑手没有按时到达,就有赔付的政策。
接下来,平台进入了算法的“垄断生产与黏性使用”阶段。平台推出了多样服务,如灵活的配送模式和更广的服务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独家经营权制度,即站队经营,流量倾斜,黏性培养。最后剩下的两大外卖巨头形成了一种鹬蚌相争没有渔翁的市场格局。
孙萍认为,外卖平台的算法空间生产牵涉到不同的利益角逐、资源争夺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展现了一种从“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过程。
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职业性别隔离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梁萌发现互联网平台劳动展现了一种显见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例如,家政业主要以女性劳动者为主,女性从业者约占95.5%,而外卖行业主要以男性为主,男性从业者约占90%。
她举例说,外卖平台的争抢订单的派单游戏迎合了男性喜爱竞争的行为特征,此外,平台会给抢单较多的外卖女骑手贴上“女汉子”的标签,塑造了人们对于外卖行业的刻板印象,这导致一部分女性主动将外卖员职业的可能性排除。
梁萌也回顾了性别意识的相关研究。在城乡流动就业早期,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但资源分配本质仍然是传统路径。外出打工以男性为主,留守女性从事农业活动;在世界工厂时期,工厂利用传统女性身份与文化,以军事化管理与传统父权制男性气质高度一致的强硬性、攻击性的监管方式,构建出一代顺服、温情的打工妹群体。
在家庭内部,经济自主性使女性开始具有话语权,男性则在自身边缘经济位置的结构性制约下做出了实用主义的男性气质妥协。而到了现在的平台劳动时期,则形成了一种“外卖小哥-家政大姐”的职业性别隔离。
梁萌此次的研究问题便是这种性别隔离是否全然是传统的延续?她试图在“具体情境”中的回答这个问题,强调个体身份的多元性、情境性和主体性。
梁萌发现,新生代的农民工往往成为了平台经济的劳动力蓄水池。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往往是由祖辈照料大的留守儿童,祖辈受到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使得女童更多负责承担家务,男童在成长过程中总能够享受闲暇娱乐。这使得新生代的男性农民工有着向往自由、不确定性较高、频繁跳槽的新特性。这恰好与平台的劳动环境比较契合。
从“外卖小哥和家政大姐”的劳动形象建构来看,平台用工使性别身份和年龄身份成为关键要素,也是人们形成对该职业劳动者主流认知的重要基础。企业形塑和主流认知又反过来影响潜在劳动者的职业选择。
因此,梁萌认为职业性别隔离并不是自然的延续。通过固化已有的分工,建构性别化的职业气质,建立惩罚越轨者的机制,职业性别隔离得以形成,是客观工作条件和平台主观建构的双重后果。
特别是对于需要从头开始建构稳定劳动者队伍的外卖业,通过以上一系列机制,与作为潜在劳动力“蓄水池”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具传统男性性别气质、向往自由、适应不确定性,排斥枯燥单调的机器生产等“新特性”产生呼应,从而将他们顺利吸纳进来。
最后的结果是,平台劳动看上去是新型用工模式,但是内核却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是性别隔离。
对于平台的相关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阳教授评议道:首先要界定平台这个概念,比如首先要厘清网络数字中介平台和经纪公司有什么区别,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此外,在数字平台时代,一些行业平台已经形成了双寡头的垄断,比如外卖平台的市场份额绝大部分由两家掌控,而我们不得不在平台上生活,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和平台的关系问题。
社科院研究员卜卫评议了性别相关的研究。她说,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中国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歧视”的定义,我们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这个概念,也需要建立起性别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
责任编辑:李昂
格力推出公司史上最大规模员工持股计划
来源:广州日报6月20日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审议通过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宣布推出不超过30亿元的员工持股计划,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据了解,多达12000人的员工持股计划,是格力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员工持股计划。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许晓芳董明珠拟出资金额上限约为8.3亿元0002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关于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特此公告。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2021年7月2日责任编辑:张亚楠0001独家|金康赛力斯CEO余海坤被免职,上任8个月小康股价最高涨6倍
余海坤在任不足一年母公司股价暴涨超6倍,此时被免职在内部人士看其“任务已经完成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小康股份”,股票代码“601127”)多名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小康股份旗下金康新能源汽车公司(下称“金康新能源”)CEO余海坤于上周“被免职”,该职务由董事长张兴海担任,而余海坤则担任董事长助理和经管会委员。0000华为欲入股北汽极狐 未来双方将联手推4-5款HI版自动驾驶车型
每经记者范文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华为正在尝试收购本土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部门,包括寻求控制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旗下的电动车品牌——极狐ARCFOX。对此,北汽蓝谷董事长刘宇拒绝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应此事。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汽蓝谷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双方确实在密切接触,但华为不太可能控股北汽极狐,入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0001